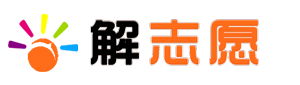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及展望
中国的现代格律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曾经辉煌的历史顶峰到现在的倍受冷落,格律诗沉默了。到底中国现代格律诗还有没有发展的前景?本文正是从中国现代格律诗自身的生命力、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人们的接受心理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中国现代格律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中国现代格律诗 生命力 诗歌规律 人们接受心理
诗,是人类生命自强不息的搏动,是世界丰富优美的回声。它和音乐一样,是形式的和谐,心灵的律动。真正美好的诗篇,应当使人感受到一种力,一种爱,一种永恒的精神。
对于诗人而言,心灵的呼声不仅表现在诗的内容上,也体现于诗的形式之中。形式是心灵的节奏,它应当微妙地传达出人类心灵深处的精神、意境、情调和幽韵。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充斥当今诗坛的更多的是一片“自由化”的喧嚣声,那些音韵优美、节奏强烈的格律诗声已完全被这混乱的喧嚣所遮盖,当代诗歌坠入了非艺术的深渊。面对当代的诗歌这一窘境,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在新诗创作过程中,“自由化”是否就真的是中国新诗的终极追求,它是否需要一些理性的规范,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诗歌格律传统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我想,新诗发展的历程及现状都会做出肯定的回答,那就是中国现代格律诗还存在,必须存在,并且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一.从中国现代格律诗自身的生命力来看
从诗歌的形式上来看,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就是诗歌格律化的一个过程。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初期,诗歌渐渐完成了由乐府诗到古体诗再到近体诗的演进。期间,齐梁诗人对音韵的重视,唐初诗人对对仗的讲究,都成为促使近体诗萌生的重要动力,而演进的内容和结果,就是诗歌格律的日趋严密,并最终产生了标志唐诗鼎盛的七律和绝句。发展到了宋词和元曲时,格律就日臻完善和更为成熟。由此可见,格律诗作为一种传统的诗体得到继承,证明格律的审美属性有可承袭的因素。
在自由体新诗崛起兴旺的新时期,又有格律、半格律体新诗的产生和发展,说明格律诗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时代要求而进行的自我调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崇尚白话和自由体作诗的同时也发出格律化的呼声,提倡新诗“第一要有格律,第二要有韵脚”[1],以汪静之、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刘梦苇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对白话自由体新诗扬弃的过程中对现代格律诗体建设规律进行探索,其意义在于,在白话自由新诗体尚不成熟的基础上转而探索建立现代格律诗体的可能性,从而为年轻的中国新诗开拓一条新的体式发展之路。到了“新现代诗派”,唐祈、杜运燮等人在注重承袭中国“象征派”诗人自由体诗的同时,又师法西方的古典诗律,将自由和格律在他们的诗作中进行有益的探索,滋润了新诗的生命。十七年诗歌创作的对格律化追求也是非常明显的,许多诗人如田间、闻捷、贺敬之、郭小川、张志民等,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创作了许多格律诗和半格律诗,丰富了格律化的新诗体式,从而将现代格律诗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可惜这一悠久的文化传统到了“文革”时期被断然否定,经半个世纪积累起来的现代格律诗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在后来的“归来”之风中又得到了全面的复兴,“归来的诗人”中的屠岸、吕剑、公刘、流沙河等诗人为现代格律诗的复兴所进行的创作实践,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一次深刻总结和重新出发,这样的实践对后来8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如胡乔木、黄淮等人的现代格律诗创作又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些诗人所进行的创作探索,证明了现代格律诗具有可承袭的审美特性以及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从中国诗歌格律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格律诗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旧格律诗,实现了一场从内容到形式的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现代格律诗,指的是‘五四以来继承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借鉴外国诗歌格律的长处,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和新诗特定的格律条件下,经八十多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逐步发展起来并日趋成熟的一种新的格律诗。”[2]总之,以闻一多、徐志摩、汪静之等为代表的“新月社”诗人和后来受他们影响的部分诗人,作为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其突出的特点和贡献就在于选择了一条探索现代格律诗的道路。这样的选择既是时代的必然,也是诗歌发展的需要。“作为诗歌形式美质的格律对于提高诗歌的表现力,在诗的本质方面和在诗歌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现代格律诗的发展与探索不是一次性的,“新月社”诗人们创造的韵律与新格律诗体将以某种方式存活下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诗人身上,它们必将复活并将继续得到新的发展,而这正是现代格律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二.从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看
诗歌首先是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精炼严整的整体要求,使得中国的诗、词、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格律。到了近代,当这种格律沿袭影响人们情感的抒发、拘束了诗人们诗意的表达时,打破格律、追求自由的要求自然成了主导的倾向,它是?极的、进步的,于是便出现了自由体新诗。因此从诗体发展的意义上讲,崇尚自由的“初期白话诗”,是以对传统格律诗体的否定来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史意义的。但由于当时的倡导者只注重打破传统格律的桎梏、解放诗体,而忽视了诗歌所特有的形式美,致使诗歌创作出现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人们又对“初期白话诗”形式上杂乱无序、过于自由散漫表示不满,于是在探索中不断地改进和发展,试图用格律化来约束和规范新诗过于追求自由化的倾向。于是有了闻一多、徐志摩、何其芳等诗人提倡现代格律诗,注重诗的形式美,并由“新月社”和之后的诸多诗人加以实践;戴望舒在感觉到自由诗的局限后,也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开始向格律诗作某种程度的回归,并将自由诗和格律诗作一种相互的渗透,以使自由诗不至于散文化,格律诗又不流于形式化;袁可嘉的诗虽有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但因其诗歌风格的活泼、流动,所以格律非但没有束缚诗情,反而在形式的严谨和诗情的奔放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和谐,这种“矛盾”的“综合”特征,既体现了诗人在格律与自由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显示了新诗成熟的一个方向;提倡散文美的艾青在重返诗坛以后,诗歌创作虽然还保持着舒缓自由的节奏,但形式上却明显地趋向于严整;以自由诗为追求的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复出后的诗歌也明显地趋向于严整;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们高举起散文美的旗帜,反对传统诗歌的体式规范,但他们的许多诗在节与节、句与句之间往往对仗工整,节奏韵律也很有规律。这些自由诗派诗人在创作中对格律无意识的运用,是因为音乐美、建筑美是诗歌形式美的规律性要求,因而在创作中也就形成了诗歌思维的某种规律。
所以中国新诗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对旧的格律诗词的破除和否定,但也潜在着对新的形式美的追求和探索。这种探索大致形成了我国新诗的两大流派??自由派和格律派:自由派要求不断打破诗歌旧有的格律体式规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种强烈的自由创新意识;而格律派则一直在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上企图改变新诗散漫无依的状态,寻求建立新诗格律的途径。因此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作是自由体和格律体矛盾运动并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正是这种矛盾统一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诗歌的历史告诉我们,诗歌体式就是在不断地打破规范和建立规范的矛盾统一中形成的,既需要自由表达的自由体新诗,也需要规范严整的现代格律诗。
因此,无论是格律派还是自由派,都意识到诗应该有一定的节奏、韵律和建筑结构,可以说这是诗歌体式的基本要求。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无法摆脱形式,也就无法摆脱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在“自由”和“格律”之间追求诗美的过程,也就形成了“自由”和“格律”不同的诗歌体式,“自由”和“格律”作为诗歌体式发展中矛盾的两个倾向,当其中一种倾向的追求过于极端时,另一种倾向就会出来纠正前者的偏颇,寻求某种平衡,使得诗歌体式在这种矛盾的张力中发展、前行。唐?在他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自由化和格律化运动》一文中就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诗从自由化到格律化是个运动、发展的过程。寻求新的格律、新的样式来巩固、提高自由化的突破成果是必要的,从自由化的奔突到格律化的凝练是一个辨证的探索和巩固的过程,一个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又统一的过程。”[4]
这既是诗歌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是诗歌历史发展的潜在规律。
三.从人们的接受心理看
诗歌是时代的感应神经,时代变化的信息往往从诗的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来。作为诗的国度,中国古代不仅留下了丰富的诗歌遗产,同时也形成了严整的诗歌体式。但到了现代社会,一些诗人却把理性的规范完全抛弃,借诗歌“自由化”之名冠冕堂皇地混迹于神圣的诗歌殿堂。难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说现在的诗歌根本读不懂,“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面对当今备受冷落的诗坛,中国新诗的发展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多能被广大读者接受并喜爱的诗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几千年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一直为每一个中国人所骄傲和喜爱。其中以律诗、绝句和词牌、曲牌为代表的古诗词格律,是建立在古汉语的声调、音韵和构词方式的基础上,以古人和谐、恬淡的审美心态为依据,而创作出众多音韵优美、格律严整的诗篇。古代格律体诗的这种审美属性在现代格律诗上得到承袭和发展,也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和诗歌自身的要求。因为,一方面诗歌作为内心情绪的感发,激荡的内在情感有它的节奏韵律,自古以来中外的诗歌都讲究韵律,并且形成严整的音乐美和建筑美的格律;另一方面形式美也有它的独立意义,它能使内容出现呈现出更完美的形态。所以,诗歌有它的体式的要求是应该的,这既符合诗歌艺术的自身特点,也符合大众对诗歌的审美心理。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格律诗派,“新月社”诗人们创作的格律诗至今为人们所喜爱,这说明了现代格律诗符合了人们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审美心理。后来的何其芳、田间、贺敬之、张志民等诗人,将现代格律诗扎根于民族语言的土壤中,深入到群众中去,在民间的民歌传统中探寻民族化格律形式,这种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来的现代格律诗,自然更符合新时期人们对诗歌的审美心理。80、90年代依然有不少的诗人坚守着现代格律诗这片领域,在一片追求诗歌“自由化”的喧嚣声中,这种坚守显得尤为的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创作中不断地改进格律诗理论,当代诗人黄淮创作的长篇微型格律组诗、丁芒的一些“自度曲”、林庚的“九言体诗”等,这些诗人对现代格律诗的探索和改进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们与时俱进的审美心理。
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时代观念和人们思想的逐渐开放,使人们倾向于追求自由而不愿意受到框框条条的束缚,所以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便成为了当今诗人的终极追求。一些所谓的诗人在“自由化,是新诗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脚步”这样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创作了一些所谓的“诗”。如下面的这一首题为《运气》的诗:
从这所谓的“自由”诗我们可以看出,当今诗坛一些诗人的创作为了行心之所向往的“自由化”,解构了古典诗歌的意象、意境等诗学追求,也解构了传统诗歌积累下来的一切修辞手段和形体建构,运行的是一种混乱的,莫名其妙的诗学尴尬,他们创作的一些诗歌在诗行排列方式上散漫错落,分段不分行者有之,一段近百字无标点者有之,排成“菱形”“三角形”者有之,一句诗横排竖拐弯排排出各种行图者亦有之,故意追求一种自由排列而造成的对视觉的冲击,这都缘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宣告一切体式追求的“荒谬”,是对以往诗歌体式的彻底摆脱。这首诗本身已无什么诗意,全然不见诗美给人造成的心灵的震撼、共鸣和值得回味的艺术感受,它只能借助错落的诗行排列企图在读者心中留下一点足音,这恐怕也是徒劳的。
又如周伦佑的这首《头像》:
欲速则不达。超现实之轮南辕北辙。你嘴上不再悬河。对某些问题可以避而不谈。托之以牙痛。或者期期艾艾。假装口吃。也可答非所问。王顾左右而言他。魏晋多清淡之士。多因嘴招致灭族之祸。你无贤者朋。但有娇妻稚子,还是少说为佳。
在这里,作者在?言上追求“大白话”,写“零度直白诗”,根本不讲究诗的节奏和韵律,只醉心于自由心灵的释放,极尽所能地任意播散和堆砌无边无沿的能指符号,诗歌语言、体式的破碎性、零散化和随意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诗歌内涵和艺术美感已经被彻底地消解掉了。
当代诗坛一些诗人创作的这些所谓“自由化”的诗歌,疏远了群众,冷漠了社会,完全把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排斥在了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借追求心灵的自由之名不负责任地放纵自由联想,去追求纯粹的“自由化”创作,结果坠入了“极端自我”、“混乱”、“散漫”的“自由怪圈”中。何其芳曾这样表达过他的观点:现代生活更适于自由诗表现,但不是一切生活都必须用自由诗来表现,更不是一切读者都满足于自由诗。如果没有适合现代语言规律的格律诗,将是一种偏枯现象。因此,在当今诗坛不仅需要自由诗,也需要格律诗。
中国新诗虽然不会被格律所束缚,但却潜在着一种格律化要求。从1926年“新月社”的成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中国现代格律诗逐步地建立、发展和成熟起来。我们坚信,现代格律诗的前景是光明的,将会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在当代诗坛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