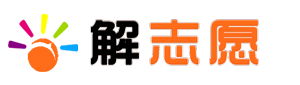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
来源:解志愿时间: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
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其最受欢迎的作品。作为一部小说,其主体讲述了几对男女间的故事。然而精彩并不在于此,故事中不断地穿插有富于哲学意味的话,而其哲学精神更是贯穿于作品全部,为作品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大抵也是这部作品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伯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小说的开头,并不急于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场景,接着引出主人公的出现,而是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尼采和哲学家们感到困惘的概念??众劫回归。“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而实际上“众劫回归”只是一种想象。如果它真的存在,在作者看来,那“原罪说”无疑会使人人的生命变得无比沉重:耶稣不断地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断地为我们受苦,而我们也因于此背负着更大的罪恶。说起来,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这位创造出人类,教人类盖房子,教人类观察日月星辰,分辨四季计算时间,教人类饲养牲畜来为自己服务,更为人类带来火种的神,却因自己对人类的好惹怒了宙斯,被宙斯派人押到中亚细亚斯库提亚荒山野岭,用永远不能开启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岩的峭壁上。宙斯还派了一只鹰不断地叼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又让他的肝脏不断地愈合。这便可以说是对“众劫回归”的最早的想象。由此看来,“众劫回归的确是沉重的。
正因为“众劫回归”的不存在,我们才能试图用我们只出现一次的生命作为辉煌与之抗衡。
也正是因为“众劫回归”的不存在,一切事物只是一次性的,瞬时的,我们才会更易于被其缓解环境所麻痹,我们生命中曾经犯下的罪恶,都被我们预先的原谅了。
那么,选择轻,还是重呢?主人公托马斯成为这一问题的代询者。
离异的托马斯是一名外科医生,个人生活放荡不羁,与多个女人保持着“性友谊”的关系。直到特丽莎出现,事态才有所变化。这个既非妻子,也不是情人的女人,在托马斯看来只不过是“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然而这个女人却让他迷茫,迷茫着是要继续“努力创造着一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还是与之结合。
选择前者,就选择了轻,也选择了托马斯可以自视为辉煌的东西;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他要和特丽莎在一起过一辈子,日子就将不断地重复,无疑,这一选择将是重的。
托马斯也试图挣脱那日益附于他身上的沉重。在娶了特丽莎之后(虽然是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才结婚的),托马斯还是出轨了。七年之后特丽莎的出走,将托马斯重新置于自由,让他再一次感受到生命之轻。可是,随之而来的沉重却将他击垮,他已经学会感受他人的痛苦,他终于明白,他再也无法回到从前虚无缥缈的生命了。而另一方面,特丽莎也不想给托马斯施加过多的负担,她明白托马斯要真的对她不忠的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当这一切真实发生的时候,特丽莎才发现,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她也尝试着走向轻,去背叛托马斯,但实际这却让她背负上更为沉重的负担。特丽莎太过认真,认真是她的行为方式,这也让她最终失败,只能选择永远的重。
当我们试图用人生的全部辉煌,即所谓的轻去抗衡重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成功吗?
肉体与灵魂,是人类以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人类总是理想化地希望自己的灵肉统一,以把握一个更为真实可感的自我,然而,昆德拉却以一个特定的性爱情境,揭示出灵与肉的分离,使人类再次陷入对自我的无把握中。
在托马斯看来,灵与肉是可以割离的。在发明“性友谊”之初,托马斯就告诉情人们,唯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www.gkjzy.com)最后他还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岂止不同,简直对立。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激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
而特丽莎则追求灵与肉的统一,她无法忍受丈夫的不忠,这让她陷入了永久的痛苦,直至死才得以解脱。托马斯和特丽莎之间的冲突,至少存在灵与肉的冲突。那么,是选择灵,还是肉呢?
何所谓媚俗?小说中《伟大的进军》就是专门讨论媚俗的。它首先从“粪便”开始,并列举了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例子。在作者看来,德国长官拒绝讨论粪便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媚俗。媚俗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场景,而试图去躲避它仅因为它带有被人赋予的并不光彩的成分是极其不正确的。
那么能否理解特丽莎的行为也是一种媚俗呢?特丽莎不喜欢母亲在家中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也不喜欢自己在洗澡的时候继父突然闯进浴室来,这在她成年后也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有一次她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投稿的时候,另一个妇女也是拿着一堆裸体人像的照片。或许昆德拉是借这个妇女之口对特丽莎进行讽刺,她说:“裸体可没有错。”“这些都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东西都是美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因为如此来讲,我们自己也是媚俗的了。然而我们真是媚俗的吗?还是我们怯于承认罢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英文版是“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有人对“Being”这个词也生发出疑问,因为作为“存在”,“Being”这个词完全可以替换成“Existence”、“Life”等,但作者终究没有那样做。这或许也是受到《哈姆雷特》的影响,在这里,“Being”已经不单单是指活着,而是针对生活中生发出的各种问题作出的抉择。
有人说,看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里面的细节都是精心铺设的。我留意到,托马斯为了给特丽莎解闷,特意给她找了只小狗卡列宁解闷。陪伴了特丽莎十年的卡列宁,最终也将离她而去,只是,看似还可以守在主人身边更长的日子,却因为癌症让卡列宁不得不和特丽莎提前说再见。
在卡列宁弥留于这个世界之际,特丽莎和托马斯都在犹豫要不要对它施行安乐死。如果狗也能听懂人的话,能有自己的思想的话,将这一抉择交给它,恐怕就不会让特丽莎和托马斯为难。可是这一切只是想象,卡列宁是否要早一点离开,主动权不在它本身,而在于托马斯和特丽莎。出于私心,特丽莎必然是希望卡列宁能多陪伴她一些时日的,可是对受病魔折磨着的卡列宁而言,早一点死去或许是一种解脱。最后托马斯,打破了这种僵化不愿改变的局面,他到底还是为卡列宁施行了安乐死。
昆德拉对这一部分的描写也是十分细致的,仿佛是为了更好的让读者感受到特丽莎与托马斯的为难。这并非是“非如此不可”,所以究竟选择轻或重,灵或肉,政治还是媚俗,存在还是灭亡,beingornottobeing,昆德拉到了最后也没有明确表示该怎样做。虽然如此,倒也不是无迹可寻,或许小说是为我们暗示了究竟该怎样选择的,只是这光芒过于幽暗,对于未来,还需要我们自己做出抉择。
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其最受欢迎的作品。作为一部小说,其主体讲述了几对男女间的故事。然而精彩并不在于此,故事中不断地穿插有富于哲学意味的话,而其哲学精神更是贯穿于作品全部,为作品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大抵也是这部作品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伯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小说的开头,并不急于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场景,接着引出主人公的出现,而是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尼采和哲学家们感到困惘的概念??众劫回归。“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而实际上“众劫回归”只是一种想象。如果它真的存在,在作者看来,那“原罪说”无疑会使人人的生命变得无比沉重:耶稣不断地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断地为我们受苦,而我们也因于此背负着更大的罪恶。说起来,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这位创造出人类,教人类盖房子,教人类观察日月星辰,分辨四季计算时间,教人类饲养牲畜来为自己服务,更为人类带来火种的神,却因自己对人类的好惹怒了宙斯,被宙斯派人押到中亚细亚斯库提亚荒山野岭,用永远不能开启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岩的峭壁上。宙斯还派了一只鹰不断地叼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又让他的肝脏不断地愈合。这便可以说是对“众劫回归”的最早的想象。由此看来,“众劫回归的确是沉重的。
正因为“众劫回归”的不存在,我们才能试图用我们只出现一次的生命作为辉煌与之抗衡。
也正是因为“众劫回归”的不存在,一切事物只是一次性的,瞬时的,我们才会更易于被其缓解环境所麻痹,我们生命中曾经犯下的罪恶,都被我们预先的原谅了。
那么,选择轻,还是重呢?主人公托马斯成为这一问题的代询者。
离异的托马斯是一名外科医生,个人生活放荡不羁,与多个女人保持着“性友谊”的关系。直到特丽莎出现,事态才有所变化。这个既非妻子,也不是情人的女人,在托马斯看来只不过是“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然而这个女人却让他迷茫,迷茫着是要继续“努力创造着一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还是与之结合。
选择前者,就选择了轻,也选择了托马斯可以自视为辉煌的东西;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他要和特丽莎在一起过一辈子,日子就将不断地重复,无疑,这一选择将是重的。
托马斯也试图挣脱那日益附于他身上的沉重。在娶了特丽莎之后(虽然是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才结婚的),托马斯还是出轨了。七年之后特丽莎的出走,将托马斯重新置于自由,让他再一次感受到生命之轻。可是,随之而来的沉重却将他击垮,他已经学会感受他人的痛苦,他终于明白,他再也无法回到从前虚无缥缈的生命了。而另一方面,特丽莎也不想给托马斯施加过多的负担,她明白托马斯要真的对她不忠的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当这一切真实发生的时候,特丽莎才发现,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她也尝试着走向轻,去背叛托马斯,但实际这却让她背负上更为沉重的负担。特丽莎太过认真,认真是她的行为方式,这也让她最终失败,只能选择永远的重。
当我们试图用人生的全部辉煌,即所谓的轻去抗衡重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成功吗?
肉体与灵魂,是人类以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人类总是理想化地希望自己的灵肉统一,以把握一个更为真实可感的自我,然而,昆德拉却以一个特定的性爱情境,揭示出灵与肉的分离,使人类再次陷入对自我的无把握中。
在托马斯看来,灵与肉是可以割离的。在发明“性友谊”之初,托马斯就告诉情人们,唯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www.gkjzy.com)最后他还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岂止不同,简直对立。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激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
而特丽莎则追求灵与肉的统一,她无法忍受丈夫的不忠,这让她陷入了永久的痛苦,直至死才得以解脱。托马斯和特丽莎之间的冲突,至少存在灵与肉的冲突。那么,是选择灵,还是肉呢?
何所谓媚俗?小说中《伟大的进军》就是专门讨论媚俗的。它首先从“粪便”开始,并列举了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例子。在作者看来,德国长官拒绝讨论粪便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媚俗。媚俗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场景,而试图去躲避它仅因为它带有被人赋予的并不光彩的成分是极其不正确的。
那么能否理解特丽莎的行为也是一种媚俗呢?特丽莎不喜欢母亲在家中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也不喜欢自己在洗澡的时候继父突然闯进浴室来,这在她成年后也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有一次她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投稿的时候,另一个妇女也是拿着一堆裸体人像的照片。或许昆德拉是借这个妇女之口对特丽莎进行讽刺,她说:“裸体可没有错。”“这些都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东西都是美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因为如此来讲,我们自己也是媚俗的了。然而我们真是媚俗的吗?还是我们怯于承认罢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英文版是“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有人对“Being”这个词也生发出疑问,因为作为“存在”,“Being”这个词完全可以替换成“Existence”、“Life”等,但作者终究没有那样做。这或许也是受到《哈姆雷特》的影响,在这里,“Being”已经不单单是指活着,而是针对生活中生发出的各种问题作出的抉择。
有人说,看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里面的细节都是精心铺设的。我留意到,托马斯为了给特丽莎解闷,特意给她找了只小狗卡列宁解闷。陪伴了特丽莎十年的卡列宁,最终也将离她而去,只是,看似还可以守在主人身边更长的日子,却因为癌症让卡列宁不得不和特丽莎提前说再见。
在卡列宁弥留于这个世界之际,特丽莎和托马斯都在犹豫要不要对它施行安乐死。如果狗也能听懂人的话,能有自己的思想的话,将这一抉择交给它,恐怕就不会让特丽莎和托马斯为难。可是这一切只是想象,卡列宁是否要早一点离开,主动权不在它本身,而在于托马斯和特丽莎。出于私心,特丽莎必然是希望卡列宁能多陪伴她一些时日的,可是对受病魔折磨着的卡列宁而言,早一点死去或许是一种解脱。最后托马斯,打破了这种僵化不愿改变的局面,他到底还是为卡列宁施行了安乐死。
昆德拉对这一部分的描写也是十分细致的,仿佛是为了更好的让读者感受到特丽莎与托马斯的为难。这并非是“非如此不可”,所以究竟选择轻或重,灵或肉,政治还是媚俗,存在还是灭亡,beingornottobeing,昆德拉到了最后也没有明确表示该怎样做。虽然如此,倒也不是无迹可寻,或许小说是为我们暗示了究竟该怎样选择的,只是这光芒过于幽暗,对于未来,还需要我们自己做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