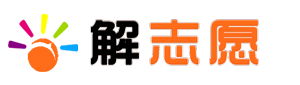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2017诺贝尔文学奖得主_2017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_诺贝尔文学奖2017作品
2017诺贝尔文学奖,暂未公布!欢迎收藏本页,小编会第一时间跟踪报道!
诺贝尔文学奖:鲍勃?迪伦
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终于尘埃落定,
没想到获胜者竟然是他??鲍勃?迪伦,这是属于摇滚的胜利!
人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大都与书桌和等身的著作有关,但是,有一个提名者却打破了这种陈旧的想象,以为他与书和书桌都毫无关系,他毕生所做的也只是拿着吉他、吹着口琴,在一群躁动不安的年轻人面前唱着快要走调的歌而已。又或者,变成海报上的一个符号,被锁在一个垮掉的时代里,同时又不在任何时代中,因为他总能让自己避免成为时代的陈词滥调。
而现在,一切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变成陈词滥调,传播让这种变化变得可能。甚至于诺贝尔也已经变成了一种一年一度的废话。这种废话与文学对陈词滥调的摒弃形成了新的反讽。对此,与其正襟危坐,不如听几首歌。
试想一下,如果这时候,一个背着吉他的老头走上来,或许嘴边还架着一只口琴,这是否会对这种神圣的气氛产生一种亵渎?然后他用一种非常不悦耳的声音唱起歌来,那神情和几十年前他身处某个露天音乐节时表现出来的毫无二致。
这种怪诞感或许反而会唤起人们对于文学的一种遥远又切近的亲切,遥远来源于诗与音乐还没有分离的希腊时期,而切近则与现代文学带着的亵渎与冒犯意味有关。文学始终是既新又旧的,它在历史的进程里从来不甘于守卫古典的范式,但革命的结果又总呼应着那些经典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鲍勃?迪伦与文学的契合丝毫不亚于任何端坐在书房里的大写作家。
诗人提名诗人
首先将诺贝尔与鲍勃?迪伦联系起来的是艾伦?金斯堡,同为诗人的他对于鲍勃?迪伦非常赞赏,还曾一同与后者去拜祭那个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先锋人物??凯鲁亚克。金斯堡为迪伦写了一封推荐信,后来由戈登?鲍尔拿着去代表竞选委员会正式为鲍勃?迪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鲍尔说:“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鲍勃?迪伦与艾伦?金斯堡在凯鲁亚克墓前
作为艺术中最抽象的形式,音乐的神秘感与诗歌不谋而合,它们都唤醒了意识中的一些临界的部分,最终无法被合理地阐释。诗歌带有呓语的特质,在古希腊还常常与预言关系紧密。柏拉图的《伊安篇》指出,诗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神,这是神对于人的恩赐,在迷狂状态下,诗人写出诗歌。在尼采这儿,代表非理性的酒神精神即是音乐精神,而诗歌的内在源泉也来源于此,它象征着人类的癫狂与痛苦,在理性的日神外表下的悲剧内核,这种精神是对虚无的顿悟,也伴随着随之而来的崩溃。
来自格林威治的异乡人
这种酒神的景观,弥漫在六十年代的格林威治的咖啡馆里,那里挤满了疯子以及过来观望疯子的人群,着迷于凯鲁亚克疯人叙事的鲍勃?迪伦拿着一把吉他,开始在这些人群中演奏。那是美国最疯狂的一个时代的开端,战争已进入疲乏的阶段,怀疑日复一日地增长,年轻人在酒馆里歌唱或者在高速公路上狂奔,预示着某种变化正在发生。鲍勃?迪伦赶上了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正如托德?海因斯后来为其拍摄的传记电影《我不在那儿》(I’m NotThere)中的赶火车隐喻一样,他开启的是一段漫无终点的游荡。
鲍勃?迪伦最开始演出的地方CaféWha
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没有方向的家》(NoDirection Home)的开头,鲍勃?迪伦将自己比作找寻归家路的奥德修斯,但是,他关于家的记忆并不存在,于是变成了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异乡人。异乡人的隐喻散见于现代西方文学的各个角落,卡夫卡笔下的灰色调人物,里尔克的自画像马尔特,加缪书中被送上审判席的局外人,最后,库切还把其综合,写了一本《异乡人的国度》……然而,异乡人被放在文学中总是比那些安分的本地人更加迷人,也更加聪明。也许是因为人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总是先抱有抱着观望的态度与小小的敬畏,在他们这儿,我们可以暂时从地面的生活中飞起来,或者从妻子的洗衣机中逃出来,获得一点点与自由有关的苦涩的经验。
《没有方向的家》(NoDirectionHome)
人为什么会变成一颗滚石?
对于鲍勃?迪伦来说,当他摆脱伍迪?格里思那有点忧伤的民谣小调时,他才以诗的形式真正开始自己的漂流,并用其为第二张专辑命名:《The Freewheelin'BobDylan》(《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后来被说成陈词滥调的《Blowin’Inthe Wind》,但是,初听它时,你仍然不免会为它带来的那种纯真的爆炸感所击中,它的形式和语言是天真的,这种天真在披头士那里也可以寻得一些踪迹,然而天真也是它摧毁力的来源,因为大多习惯了生活的人,总是会在天真面前感到恐惧,恐惧的来源与遗忘和漠视有关,它唤醒了一部分自我,然而又不会对此负责,或许还会引发一些孤独的症状。
很多人将这首歌与反抗以及战争联系在一起,但鲍勃始终对阐释保持沉默,这也让后人对鲍勃的形象定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在歌曲《我不在那儿》(I’mNot There)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在场,另一方面又是对无名的“她”的痛苦生活的描述,其中的“我”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种意象,它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目击者,这个目击者对人们经历的一切都无能为力。
这种不在场的目击者或许才是鲍勃?迪伦,撇开意识形态、社会运动,这些东西对于那些真实的痛苦都显得太做作了。他目睹的是谋杀,他展现的是,谋杀是如何进行的,他困惑的是,人为什么会死于这些东西?人为什么会变成一颗无所依附的滚石?
这种目击者的形象也是文学意义上的。
迪伦之名来自一个酒鬼诗人
在去纽约之前,鲍勃?迪伦选择了用迪伦为自己命名,是为了追溯那个来自威尔士的酒鬼诗人Dylan Thomas,一个预感自己会早夭于是迫切地将生命浓度增加到最强的疯子。当然,鲍勃要显得理智多了,他更注重的是Dylan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那些事情,有人会因此责怪鲍勃不够真诚,毕竟,衰老对于拥有天赋的诗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背叛。
但是,不允许背叛或许比背叛离文学更远,文学就是一个对背叛上瘾的东西,有男作家把它比作女人,命名为缪斯,她在时间的外面,挑选时间内的那个人,告诉他关于活着的全部,也就是缪斯自身,与他相爱,然后又在某一个瞬间离他而去。忠诚如果存在的话,也必须是相对的,被选者是永远的单恋者,有一部分会因此憎恨文学,但却很少会抛弃它,兰波或许算一个。托尔斯泰就显得太过老实了,他勤勤恳恳地用一辈子去服务,在最后一刻才显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诺贝尔是对失恋者的安慰奖
这样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一种安慰性的存在,为那些爱情受挫的人,颁发一种替补性的在世荣誉。文学本身不对这个世界负责,它什么也不做,大部分时间还显得十分讨厌,满篇都是连娱乐功能都无法提供的学究气十足的文字,充满了厌世情绪的消极腔调,荒诞不经的胡言乱语……在能为人类治愈疾病的医学成果或者能让人探索宇宙的物理学成就面前,文学就像个穿着睡衣的酒鬼。
为了让这个酒鬼走上殿堂,委员会做了许多努力,譬如将文学与某种叙事传统联系起来,或者让某些政治的因素掺杂进来,或者仅仅是褒扬其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以“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为由颁给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这一奖项,2007年则说多丽丝?莱辛是凭借构建起“女性经验的史诗”而摘得殊荣,当然,对于莫言,政治的考量似乎大于作品的含义。大多数人会去领受这一荣誉,以疗愈自己的心碎,但人间情人颇多的萨特显然有其他办法来平衡文学带来的失落。
索尔?贝娄曾经叫这种失落描绘得十分精准,他写了一个死于心碎的舅舅,他也同时着迷于这种心碎。他将舅舅描述成了一个可怜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懵懂的先知,同时也注定拥有悲剧命运的人,他的努力最后被人类一种更大的空虚所俘虏,并最终深陷其中。索尔?贝娄做了一次尝试或者说一次手术,医生和患者都是自己以及与自己身在同样处境中的那些人,只为证明,他们不能拯救任何人,只能像一株植物一样,在自己的生存系统中度过自己的时间。
鲍勃短暂地试图与时代交融之后,很快地便抽身走了,但时代却不会轻易地放过他,当然,也不会放过村上春树以及任何其他的索尔?贝娄笔下的舅舅。